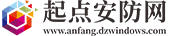专访诺兰:这一次,我没办法把牙膏挤回管内了
如果我们能够将牙膏挤回管内,倒转时间,我们是否能够不发明毁灭性的技术?《信条》是关于不去发明毁灭性技术的故事,而《奥本海默》是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答案是:不,不可以。
新片《奥本海默》上映,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主人公?
 (资料图)
(资料图)
他总是谈起奥本海默所领导的“三位一体”核试验中按下按钮的时刻:1945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虽然科学家们无法完全排除一种最糟糕的后果——爆炸之后,发生链式反应,点燃大气层,最终毁灭地球,但他们仍然决定按下按钮。之后,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核试验成功,最终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终结。
在电影里,这段情节被呈现为一次紧张的倒计时,一段25秒钟的静默,一场随之而来的欢呼,和一个科学家兴奋又迷茫的神情。
诺兰之前拍过数部科幻片,有过天马行空的想象,仍然将这个历史时刻称之为“我听到过的最戏剧化的时刻”。人类冒着巨大的风险,终于拥有了毁灭自己的能力。
他将这个时刻看做一个决定性瞬间,之后,建立在核能力之上的毁灭、制衡和发展,逐渐形塑了当今的世界。诺兰在这部电影里做了许多尝试,他希望呈现出一个天才脑海中异世界的想象,让观众能够与之共情;他通过一场审判回顾这段历史,奥本海默身上的道德困境和时代困局,是否是只应由他自己承担?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身处拥核之后的世界,电影内外,都必须去面对现实。在诺兰上一部电影《信条》里,人类制止了致命武器,《奥本海默》里,致命武器被研发出来,而这次,时间也不会倒转了。“如果造物之神能够允许我们去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将牙膏挤回管内,倒转时间,我们是否能够不发明毁灭性的技术?《信条》是关于不去发明毁灭性的技术的故事,而《奥本海默》是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答案是:不,不可以。”
以下是和诺兰的对话。
GQ报道:《奥本海默》是你第一部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电影,为什么选择这个人?为什么是现在?
诺兰:为什么是现在——在我讲述奥本海默的故事之前,我对他已经感兴趣很久了,只是现在我准备好了。别人送了我一本凯·伯德和马丁·J·舍温写的《美国的普罗米修斯》,这是一本令人惊叹的好书,他们研究奥本海默的生平25年,在事实和信息来源上可谓权威。这本书给了我讲述这个故事的自信。
至于为什么是奥本海默,我一直被他故事里戏剧性的一面所吸引。尤其是当我发现,在我上一部电影《信条》里,我还在台词里提到了他。故事的关键是曼哈顿计划,他们在其中进行了“三位一体”核试验,当他们按下按钮的时候,并不能完全排除点燃大气层、毁灭世界的可能性,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这么做。作为电影人,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戏剧化的时刻。
GQ报道:你之前提到过,像《盗梦空间》《星际穿越》这样的科幻电影,你需要建立一个世界,但像《敦刻尔克》这样的电影,你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它来源于现实,你需要做的是探索。我想《奥本海默》是同样的情况,在这部电影里,你想探索的是什么?
诺兰:探索他在这些事件中的观点,探索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各种各样的道德困境、悖论,没有什么答案是容易的。我想从他的视角去看问题,更好地理解他。他和他周围的世界的确已经身处历史之中,但就像《敦刻尔克》一样,你需要找到自己的方式,去给观众建立一个有上下文语境的世界。因为我不是在拍一个纪录片,我需要做许多决定,为戏剧化的演绎负责。我需要呈现所有影响这个世界的一切,它看起来是怎样的、听起来是怎样的、在其中人们的举止是怎样的。《奥本海默》背后所有选择的指导原则是主观性(subjectivity),我需要设身处地地想象他。
诺兰在《奥本海默》片场
GQ报道:这个剧本是你用第一人称写的,为什么用第一人称?
诺兰:在我写剧本的时候,我想寻找一种将自己置于他头脑之中的方式,所以我决定用第一人称,“我这样”、“我那样”。在创作上,这种方式对我有好处。同时我发现,这也方便了其他阅读剧本的人,他们开始明白我要如何处理这部电影 。每天在片场,当我看着剧本的时候,它会提醒我如何放置摄影机,如何设计场景,彩色场景里体现的视角。黑白场景更客观,它是由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路易斯·斯特劳斯的视角。
GQ报道:这是你的写作习惯吗?
诺兰:不,我之前从未这样做过。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是否这样,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写作习惯。每个剧本,你都想寻找一种从未做过的方式,至于写作格式,你想要探索和与观众交流的是,这个电影想要做成的样子是什么、它的基调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再尝试一次。它适合这个项目,但每个项目是不一样的。
在我开始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想在视觉层面、情感层面展现他的天赋。在电影里,天赋是极其难以与人们产生关联的事情,无论你是拍摄诗人、艺术家、科学家,他们的智识和审美能力很难让人共情。他在量子物理上革命性的洞见,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将其视为魔法,几乎像(《星球大战》中的)绝地武士一样,像哈利·波特的魔法一样。他并不能够完全理解他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事情,甚至对这样的能力感到害怕。然后肯尼斯·布拉纳饰演的尼尔斯·玻尔出现了,他给他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如何控制那样的能量。我们试图让他神经官能症式的内在能量与他看到和想象的量子能量同构,并在爆炸场景中找到他自己的表达方式。
GQ报道:你提到电影中的天才与普通人之间很难建立连接,这种连接是否可以是责任感,或者私人感情?
诺兰:对于像奥本海默这样的天才而言,人们能与他共情的是道德感。某种程度上,最能让人共情的是当事情出了问题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像奥本海默那样想事情,但我们能够像他那样去感受,感受他面对的道德困境、左右为难的情况。对我而言,与这个角色共鸣的重要节点是电影中段的时候,他成为“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召集各式各样的人为一个既定的目标工作。我的工作也有类似之处。让观众能与奥本海默共鸣,是这部电影很有挑战的地方,我想基里安·墨菲富于智慧和感情的表演,能够让观众感受到这一点。他让我们进入了奥本海默的世界。
GQ报道:你觉得和他在智识上有共鸣吗?
诺兰:不,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想事情。不过我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基普·索恩(Kip Thorne)在几部电影里合作过,最开始是《星际穿越》,他需要给我解释一些科学原理。他说得很清楚,对科学家而言,理解一种重大的突破会改变你思考的方式。这不仅仅是关于智识、数学,他们需要直觉。他们需要感觉到他们理解了一些东西。他们需要像作家一样能够去构思。于是,我与奥本海默又多了一些共鸣点。这是为什么我在电影里会如此呈现他理解物理的方式,非常视觉化,非常情绪化,更像一位艺术家。
这是我从基普身上发现的,事情也许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分得清,灵感就是灵感,直觉就是直觉。科学家依赖直觉,这部分我与奥本海默有共鸣。剩下的部分,就像我与基普的交流一样,只能理解到那里了。他们生活在一个我和观众无法理解的智识世界里,也正因为我不理解,我更能够讲好这个故事,因为我和观众的位置是一样的。
诺兰在中国(摄影:马格纳斯·诺兰)
GQ报道:对奥本海默的审判贯穿了整部电影,也是对那个历史阶段的审判。当我们回望这个审判的时候,有哪些新的维度或者视角?
诺兰:结束这场审判花了70年的时间。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能源部撤销了关于奥本海默安全听证会的结论。他们为什么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不知道,人们为此呼吁很久了。他们终于承认了出于政治原因,对奥本海默进行了不公正的审判。针对他的安全听证会是非常不规范的、腐败的,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呈现了一部分复杂性,但现实比电影要糟糕得多。
他们花了这么久时间才承认这一点,真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奥本海默在安全听证会里受到如此对待,以至于在国家层面有一种愧疚感。《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一书的副标题“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是这个故事真正的核心,我们想让观众去体会“三位一体”核试验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岛、长崎核爆的悲剧,和1945年之后发生的一切。
GQ报道:在你的两部关于历史的电影中,你都选择了一个危机时刻。《敦刻尔克》里,是英法联军的危机,在《奥本海默》里,是世界性的危机。为什么这样的危急时刻会吸引你?
诺兰:当你面对虚构作品的时候,有太多的诱惑,比如超级英雄电影、间谍电影这样的类型,你创作的主要精力在于构建对世界和人性的威胁。至于《敦刻尔克》,那个故事内在自有其张力,就是英国军队的消亡、纳粹德国的胜利和英国的覆灭。而《奥本海默》,威胁再清楚不过,我们释放出来了有史以来最具有毁灭性的力量,人类获得了毁灭自己的能力。奥本海默之前是一个世界,奥本海默之后是另一个世界。两者很不一样。这样你就呈现出了最具戏剧性的危险,对电影制作而言,这是你梦寐以求的吸引观众的故事。
GQ报道:两者也都是二战时的危机时刻。你对二战有独特的兴趣吗?
诺兰:我倒并非对二战的历史特别感兴趣。我在英国长大,在我成长的年代,二战是流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电影是关于二战的,电视上经常能看到二战的画面,我当然会注意到这些。二战对英国、对它的生存来说非常重要。《奥本海默》是一个美国故事,我也是半个美国人,所以我也会注意到二战后原子时代的开始,以及美国作为强大国家的崛起。奥本海默的故事代表了美国独特的现代化力量中伟大和可怕的东西,而这种现代化力量又是建立在破坏性的力量之上。
GQ报道:你认为人们从危机中是否学到些什么?
诺兰:我认为剧情片的目的不是为了教会人们什么。我不能假装自己知道答案,拍电影是为了提出有趣的问题,找到能让你以某种有趣方式去思考的故事。赌注越大,危机就越可怕,它对你的影响就越大,你也会对故事里表述的议题思考更深。
我认为我的工作是提出问题,呈现复杂的情况,而不是假装我有答案。奥本海默生命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答案,而这正是我有兴趣讲述他故事的原因。
诺兰在《奥本海默》片场
GQ报道:话剧《哥本哈根》里,两位欧洲物理学家讨论科学家在战争中的道德困境。我在《奥本海默》里也看到了类似的困境。
诺兰:是的,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当尼尔斯·玻尔出现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他对与海森堡在哥本哈根的谈话有自己的解释。但海森堡提出了异议,他有一个与玻尔非常不同的版本。奥本海默不知道海森堡的观点是什么,他只知道尼尔斯·玻尔告诉他的,而尼尔斯·玻尔非常确信海森堡要帮纳粹制造原子弹。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GQ报道:这两部戏中,制造炸弹的人不断反思自己,而投掷炸弹的人却没有。制造致命武器是人类的选择,还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诺兰:在曼哈顿计划中,军方与科学家的主要冲突之一是对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分裂原子的手段。对科学家来说,一旦德国人分裂了原子,他们一定会造出原子弹。他们视之为自然法则。同样的情况,也可以看建立在聚变反应之上的氢弹。科学家认为,你不能独享知识,也无法压制知识,你只能持续不断地学习知识,并与所有人分享知识。对军方来说,比如对格罗斯将军来说,这种看法是歪理邪说,太疯狂了。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囊中之物,既然能够首先制造出来,就能够独享它。杜鲁门认为能够永远独享这些炸弹,其他国家造不出来。科学家则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一旦人们明白制造武器的原理是什么,这些武器无论被用于正义的目的,还是邪恶的目的,它们的出现都是不可避免的。
GQ报道:所以这种道德困境是只属于科学家的痛苦?
诺兰:某种程度上是的。上世纪50年代,爱德华·泰勒、奥本海默等许多人有大量关于原子的讨论,他们急于尝试将原子的使用引向积极方面,比如核能,等等。其中一些设想看起来奇怪又荒唐,在一小段影像里,泰勒说可以利用氢弹挖巴拿马运河。如果付诸实践真是疯狂。当然,这也是因为这项技术在当时来说还是新鲜事。
科学家们努力尝试去强调原子弹的和平用途,希望所有人明白,这并不只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我认为长远来看,这是对的。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原子弹的毁灭性仍远远大于它的建设性。但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发生变化,技术最终将带来巨大利好。
GQ报道:在《信条》里,我们制止了致命武器,那个时间炸弹。在《奥本海默》里,我们没有能够制止,而且这次时间也不会倒转了。《奥本海默》最后一句台词是,“我们毁灭了这个世界”。你为什么会用这句台词做结尾?
诺兰:我不太想过多讨论电影的结尾,因为很多人还没看过(笑)。虽然它是一部基于历史的电影,但我希望我讲述它的方式能令人感到惊奇和不同,当然也包括结尾。《信条》是科幻片,当我回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意识到它就是关于这个炸弹的。跟许多讲时间或者时间旅行的电影一样,这是一部许愿电影,如果造物之神能够允许我们去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将牙膏挤回管内,倒转时间,我们是否能够不发明毁灭性的技术?《信条》是关于不去发明毁灭性技术的故事,而《奥本海默》是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答案是:不,不可以。
GQ报道:我们必须去面对。
诺兰:是的。
GQ报道:当我们讲述历史的时候,讲的也是当下。这部电影是给当下的观众看的。你认为奥本海默与当下的观众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诺兰:我想这个故事有很多不因时代变迁而减损的意义。这部电影是一个警示故事,警示我们科学和技术在现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宣传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和许多人聊过,我听到他们提及人工智能的兴起,并惊奇地发现,一些顶尖的研究将当下称之为他们的“奥本海默时刻”。奥本海默的故事能告诉他们什么?科学家的责任感。发明一项技术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我很高兴他们看到了这个故事。奥本海默的故事里没有容易的答案,但我很高兴他们提出了这些问题,也很高兴他们据此进行了公开的辩论,这最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安全。
GQ报道:我听说当你开始写剧本的时候,你的儿子对你说,“现在没有人关心核武器这个话题了”。但是两年后,他就不这么说了。
诺兰:是的。很不幸,这戏剧化地体现出我们对核武器的恐惧。在我的人生中,对核武器的恐惧起起伏伏。我12、13岁在英国上学的时候,核威慑非常盛行,它出现在流行文化里,是我们一直讨论和极度害怕的事情。很不幸,在我开始写剧本到电影完成的这段时间,人们又开始担心起核武器了。另一方面,我们有必要讨论如何控制这种威胁。
GQ报道:你觉得我们目前仍然面临着危机吗?
诺兰:是的。当你和了解核武器的科学家讨论的时候,对于当下核毁灭的威胁究竟是什么,他们不会给出令人安心的回答。
GQ报道:世界正在快速变化——正如你在电影里所说。作为创作者,如何让你的作品与观众息息相关?
诺兰:作为电影人,我不认为你需要过多担心。制作电影的时间太长了,如果你想追逐热点,你会不可避免地错过。对我来说,我需要选择那些真正能打动我的主题,当有人告诉我,比如我的儿子,说没有人会关心这些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电影有信念,你必须无视他们。我在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里工作,被同样的事物影响,听同样的事、看同样的事,我认为如果我忠于创作的初衷,就有足够机会创作出其他人能够感同身受的作品——我对此坚信不疑。
标签:
推荐文章
- 中迪投资录得6天4板
- 专访诺兰:这一次,我没办法把牙膏挤回管内了
- 中关村地区全民健身体育节冰上项目普及活动顺利举行
- 深新早点 | “苏拉”或正面袭击深圳!台风橙色预警生效中!
- 港交所:八号台风信号现正生效 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延迟开市
- 距今93万年前人类几近灭绝!上海科学家首次对古人类进行“人口普查”
- 安徽霍山:打造“漫宿”民宿 助力乡村振兴
- 太极实业(600667):8月31日北向资金增持161.39万股
- 8月31日基金净值:银华中证光伏产业ETF最新净值0.8709,跌1.35%
- 纳芯微:拟回购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4亿元公司股份
- 蒙牛净利润同比下降19.48%背后:毛利率在提升
- 布莱泽:最新杂志图情报,布莱泽潇洒使出雷鸣剑,阿斯加隆化身狙击手
- 日本敦贺核电站2号机组供水处理建筑内发生火灾
- 秦公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第四次发掘启动
- 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开展不乘坐违规电动三四轮车宣传
- 年金险有哪些优势?
- 受台风“苏拉”影响,株洲西站停运或区段停运列车90趟
- 国防部: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核威胁
- 联通好服务 用心为客户 河北保定白沟友谊路营业厅真诚常在 初心不改
- 山东暑期档观影数据出炉:济南票价全省最贵,超全国水平
- 8月31日冀中能源创60日新低,国泰中证煤炭ETF基金持有该股
- 外媒提前发布《星空》评测:后被B社光速删除
- 亚士创能(603378)2023年中报简析:营收净利润双双增长,债务压力大
- 2023年退休养老金计算公式包括哪些?工龄42年能领多少钱?
- 冲上热搜!济南30岁公务员辞职做短视频博主,网友吵翻了
- 舜宇集团2024届全球校园招聘正式启动!
- 【强信心 促发展】为啥姚老汉的田不旱?——金川区“解锁”农业节水灌溉新模式
- 农业农村部:统筹研究相关农产品进口关税待遇问题,支持中俄农业合作
- 碧兴物联:8月30日融资买入8189.6万元,融资融券余额1.73亿元
- 特朗普:如果重返白宫就关押政敌
- 广货精品将亮相第六届中阿博览会
- 上海:着力办好每一所家门口学校
- 保险公司:新能源出险率比油车高近 1 倍,省下的油钱都用在保费里了?
- 华为悄悄上线高端手机Mate60Pro “偷袭”苹果?
- 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正式揭牌
- 微创医疗(00853)发布中期业绩,股东应占亏损1.63亿美元 同比大幅减少18%
- 中航电测(300114):8月30日北向资金减持19.36万股
-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意思解释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意思
- 匆忙旅客错拿行李 老练乘警帮忙找回
- 天承科技:上半年净利润2613万元 同比下降1.61%
- 广州上周主要民生商品价格总体继续缓升
- 蓝莓树下的“电商梦”
- 福建平潭夜空现巨型“云环”,气象台:没见过这么规则的,应非气象云
- ColorOS 13.2出厂:Find N3 Flip系统更新及时给力
- 2023成都星电音联盟总决赛终极派对之夜禁止携带物品清单
- LOL又出了个疯批萝莉!玩家关注点全在Jio上,CG被拳头拍成恐怖片
- 电报解读|中远海能(600026.SH):运价大增推动利润增长1667.48%,Q4运价仍有望超预期
- 广播地址怎么算(广播地址)
- 浙江医药:盐酸米诺环素获得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
- 上海家化:希望Q3、Q4海外市场的跌幅能收窄到个位数
- 珍岛集团:科技生产力助力社会整体发展,创造商业和消费者便利
- 净负债率低至39.8%,美的置业2023年上半年重启拿地
- 刚刚通报:4人遇难,48人失联
- 乌鲁木齐“六馆一心”停车这样收费
X 关闭
最新资讯
- 2023年保定九月限号吗?具体规定是什么?
- 港股异动 | 英恒科技(01760)再涨超7% 获纳入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系列 公司受益智能车趋势
- 立高食品8月30日快速回调
- 【雄安之声】知名农企进雄安交流活动举办
- 郑州:“家门口”招聘 “家门口”就业
- 2023年中国·西宁高原国际风筝邀请赛举行
- 11名被任命人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职情况
- 国泰君安;需求预期改善助力,铜价或强势上行
- 有利于减轻航天飞行器重量,西工大团队打造高质量锡基钙钛矿电池
- 《鬼灭之刃》第二季开播,无限列车篇新剧情放出,花街篇12月播出
- 苹果秋季发布会定档 预计将发布iPhone 15系列
- 汉王科技(002362):8月29日北向资金增持84.39万股
- 金达威:2023年半年度净利润约1.84亿元 同比下降32.92%
- 一个月抓获58人!西安警方严厉打击演唱会“黄牛”
- 又要跳票?《浩劫前夕》疑似改名 但仍存在商标风险
- 罗国祥:我在贵州屋脊下开民宿
- 大悦城控股上半年投资物业及相关服务收入27亿元 增长34.73%
- 莱依德隆(关于莱依德隆简述)
- 技嘉推出 Z790 X 系列主板,适用于英特尔 14 代酷睿处理器
- 中国平安:2023年中期净利润698.4亿元,去年同期602.73亿元。
- 恒帅股份股东户数下降9.96%,户均持股19.41万元
- 否之匪人
- 大面积跌停后,官方辟谣!
- 王者荣耀回应活动异常:正在定位问题,功能暂时关闭
- 这些三星设备不支持升级One UI 6.0 含S20、Note 20等
- 近五年中国算力总规模年均增速近30%
- 焦点访谈丨花样解锁消暑方式 今夏清凉消费氛围足→
- 神之亵渎2升级念珠npc在哪 神之亵渎2升级念珠npc位置
- nova是什么手机
- 带着妈妈去支教 00后团代表刘羲檬把爱传递
- 市第六届运动会市直组职工篮球比赛开幕
- 海南出台规定治未成年人文身乱象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 电视播放改编的儿歌,家长:这种内容也能播?
- 到底是谁在租巴黎的房子?!你在和68万学生一起抢…
- 甘肃敦煌: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完工
- 美联储最新预测:3季度,美国GDP或增长5.9%?
- 莱布尼茨神义论思想研究(关于莱布尼茨神义论思想研究简述)
-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将于9月6日在佐治亚州受审
- 教师风采|周金宗: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 图解:除了核污染水,日本还有“无处安放”的核垃圾
- 汇丰报告:中国与中东贸易增长潜力巨大
- 风华高科:公开挂牌转让参股公司贺江电力20%股权,挂牌底价为人民币25800万元
- 近岸蛋白(688137.SH)半年报净利润1236.03万元,同比下降82.66%
- 成年奶牛一天消耗的食物和水有多少,如何合理搭配饲料?
- 血渍怎么洗掉不留痕迹(血迹怎么洗干净)
- 首批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名单公布 12家单位入选
- 机械键盘各种轴是什么意思(机械键盘各种轴的区别)
- 华鑫证券:五箭齐发,超跌反弹一触即发
- 金太阳8月28日盘中跌幅达5%
- 交银理财上半年实现净利5.95亿 同比减少6.15%
X 关闭